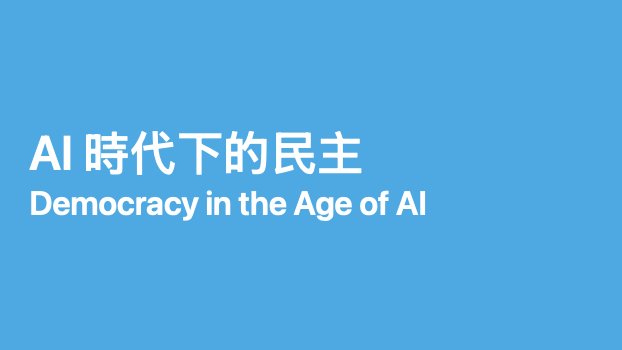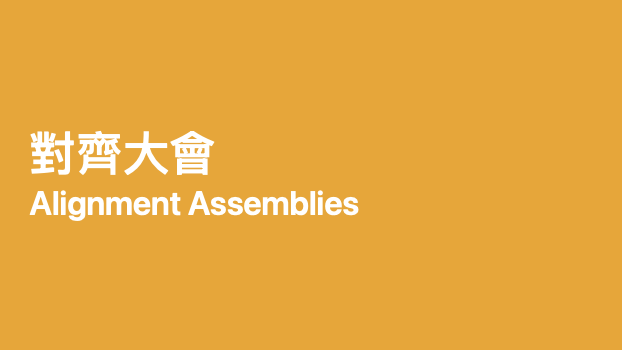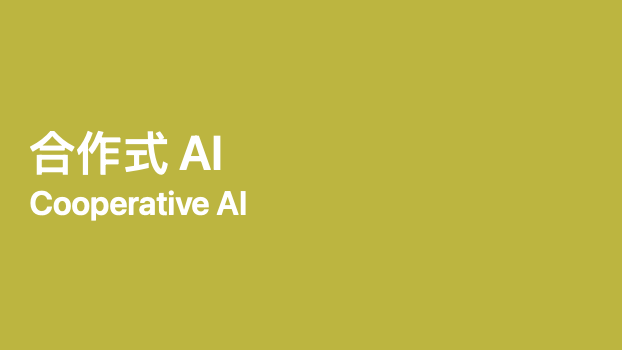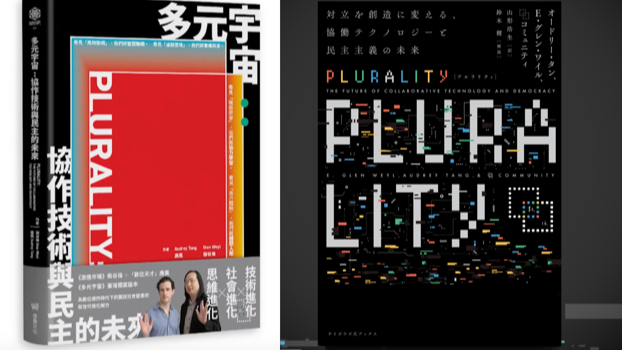AI 時代下的民主
Democracy in the Age of AI
各位好。我是唐鳳,🇹🇼臺灣的數位治理大使、首任數位發展部長。
今天,當我們談到「AI」,再談到「民主」,心中可能浮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畫面。
一種是悲觀的。社群媒體的 AI 演算法,推送充滿對立、撕裂的言論,演算法把我們推進一個個同溫層,讓我們覺得對話越來越困難。我們彷彿看到民主正在被 AI「駭侵」。
但還有另一種畫面,一種樂觀的想像。在這裡,AI 不是製造分裂的武器,而是搭建橋樑的工具。它能幫助我們跨越差異,找到意想不到的共識,讓民主變得更真實、更有韌性。
很多人覺得,面對 AI 的快速發展,未來就像一輛只有油門和煞車的車。要嘛全力衝刺,奔向未知的「奇點」烏托邦;要嘛踩死煞車,因為害怕反烏托邦的到來。
但我們忽略了最重要的東西:方向盤。
今天,我想跟大家分享的,就是這個「方向盤」的故事,也是我在牛津研究的方向:「合作式 AI」。它讓我們共同把未來,開上正確的道路。
被駭侵的民主
Democracy Hacked
這不是比喻,而是現況。社群巨頭在 2015 年前後默默換了預設:從「追蹤」(你我可共用的現實)改成「推薦給你」(AI 餵你最有黏性的內容)。
「你追蹤的內容」是一個「為我們(For Us)」的現實。如果你我追蹤同樣的人,我們看到的世界基本上是一樣的,我們活在一個共享的現實裡。
但「為你推薦」不同。它背後的 AI,是一個寄生式的 AI。它的唯一目標,就是學習用什麼內容能讓你上癮,把你黏在螢幕前。於是,每個人都活在一個為自己量身訂做的、極度個人化的世界裡。
結果是什麼?不是只有成癮,更是分裂。最能維持你停留的內容,往往是讓你憤怒的內容。這種設計非常容易被專制政權利用,透過惡意 AI 蜂群,在我們的公共場域發動心戰。
他們的目的很簡單:讓我們懷疑制度、敵視鄰人、相信民主只會帶來混亂。當大家疲憊到想放棄時,就容易受到專制擺布。
炎上流量
Engagement through Enragement
所謂「社交網路」,其實多半變成了炎上的基礎建設:它把社會最重要的「連結」拿走,然後賣給出價最高的廣告商。它精準地知道我們的喜好、恐懼和身分認同,但這些資訊,我們自己卻看不到。
這就是今天許多民主社會面臨的困境:我們不是沒有善良的人、不是沒有願意對話的人,而是我們使用的工具,在底層設計上,就不鼓勵我們這麼做。
那麼,我們能怎麼辦?難道只能放棄這些平台嗎?
不,我們可以「翻轉」這個演算法。我們要重構這些系統,讓它們從炎上,變成合作的平台,天生就能抵禦操弄。
從抗議到示範
Protest → Demo
改變的契機,來自十年前。2014 年,臺灣發生了太陽花運動。許多人佔領了國會,表達抗議。
但這場運動最特別的地方,不只是「抗議(Protest)」,更是「示範(Demo)」。在抗議現場,有一群像我一樣的公民科技專家,我們沒有花時間去想要推翻什麼,而是花時間去「打造」什麼。
我們在現場架設了網路,確保資訊的透明流通。我們做直播,讓國會裡外的對話能夠同步。我們不只說「不要什麼」,我們更用程式碼和行動,去「示範」一個更開放、更透明的民主,應該是什麼樣子。
這個經驗讓我們明白,社會運動的能量,可以不只停留在一次性的抗議,而是可以轉化為長期的、制度性的建設。從街頭的抗議,走向鍵盤上的創造。
橋接系統
Bridging Systems
那這些工具是什麼?核心概念很簡單:我們要建立一個「搭建橋樑的系統」。
我舉個例子。2015 年,Uber 剛進入臺灣,引發了劇烈的社會爭議。一邊是支持創新的使用者,另一邊是擔心生計的計程車司機。雙方在網路上吵得不可開交。
我們當時導入了一個叫做 Polis 的系統。在 Polis 上,你看不到「回覆」按鈕,你只能對別人的「感受」表示「同意」或「不同意」。
當你投票時,你的頭像就會朝與你意見相似的人群移動。很快地,你會在地圖上看到幾個主要的意見團塊。但最關鍵的設計來了: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新的想法,如果你的想法,能夠同時獲得不同團塊裡的人的「同意」,這個想法就能「跨越」群體,獲得最高的積分,在系統裡被最多人看見。
我們把「瘋傳」的獎勵,從給最極端的言論,改為給最能「凝聚共識」的言論。
最後,我們找到了所有人都同意的幾項原則,例如「計程車也可以有多元費率」、「車輛必須有保險」、「不能用無牌車」等等。這些共識,最後變成了法律。Uber 爭議,在臺灣就這樣和平落幕了。這就是尋找「罕見共識(uncommon ground)」的過程。
廣泛傾聽
Broad Listening
加州也大規模採用了這種模式,成立了「參與式加州」(Engaged California)。該平台直接受到臺灣模式的啟發,透過讓民眾參與政策制定,來解決野火災後復原、增進政府效能等迫切問題。
在危機中,完全的公平和普遍接受的妥協幾乎不可能實現。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盡可能廣泛的社會共識,防止不公平情緒引發政治阻力。政府如何避免政策反彈並與民意保持一致?AI 可以透過廣泛傾聽,來提供解決方案。
該平台的運作方式,是識別不同的人口群體,並確定對每個群體最重要的政策。例如,雖然優先考慮心理復健的民眾的居於少數——這使得該議題在傳統的預算辯論中難以獲得支持——但透過名為「Ethelo Score」的共識指標,卻能權衡支持的廣度和爭議的程度,從而降低少數族群的不滿。
這類系統會識別出重疊程度最高的優先事項,並由 AI 將這些優先事項綜合成可行的政策提案。那些被證明高度兩極化的倡議,則會被推進到下一輪審議。
青年參與
Youth Participation
所有這些創新背後的引擎,是年輕人的活力和願景。
在臺灣,民主的誕生與公共網路的誕生同時發生。我們的第一次總統直選是在 1996 年,同年瀏覽器普及。對我們的年輕一代,我們的數位世代來說,民主從來都不是一座固若金湯的紀念碑。它一直像軟體一樣:需要不斷除錯、升級和改進。
在我們的公共政策參與平台上,民眾可以自由提出政策倡議。只要收集到 5,000 個簽名,相關政府部門就必須回應民眾的正反論點。
幾年前,一群中學生利用這個平台提議將上課時間延後一小時,並以青少年睡眠的科學數據為基礎。他們收集到了簽名。經過數月的合作,教育部最終在全國推行了這項政策。
停下來思考一下這種力量。它告訴每位年輕人:你不必等到投票權才擁有發言權。你現在就擁有改變國家的力量。他們不僅是我們的未來,更是我們的現在。他們是數位民主的原生代,也是未來公民核心的創造者。
而這股能量並不限於臺灣。在日本,我們看到了像安野貴博這樣鼓舞人心的人物。這位 34 歲的 AI 工程師兼科幻作家,正在開拓數位民主的新途徑。
受到《多元宇宙》思想啟發,安野貴博在選舉前一個月競選東京都知事,並透過廣泛傾聽的工具形成政策,隨後啟動了「日本數位民主 2030 倡議」計畫——目的並非製造分裂,而是在候選人和選民之間,建立真正的對話。
安野貴博代表了新一代全球公民技術專家,他們正在打造開源工具,以建立更具參與性和透明度的社會。憑藉超過 2% 的全國支持率,他現已被選為參議院議員。
對齊大會
Alignment Assemblies
隨著 AI 的發展,我們的民主技術也在升級。最新的實驗,叫做「對齊大會」。
去年,臺灣社會被大量的「深偽詐騙廣告」困擾。很多名人,像是 輝達的黃仁勳執行長,都被冒用。社會覺得很困擾,但又擔心政府如果出手管制,會不會變成言論審查。
怎麼辦?我們用手機簡訊,隨機邀請了二十萬位公民,最後,450 位在人口統計上能代表臺灣社會的民眾,參加了一整天的線上會議。他們被分成 45 個小組,每個小組 10 個人,就像一個個「公民陪審團」。在 AI 主持人的協助下,他們腦力激盪,提出各種解決方案。
例如,有個小組說:「我們不只要對平台處以罰鍰,更要讓平台負連帶賠償責任。如果有人被深偽投資廣告騙了 100 萬,平台就要賠 100 萬。」另一個小組說:「對於在臺灣沒有辦公室的平台,我們可以逐步降低它的連線速度,抑制它的流量。」
這些來自民間的智慧,透過語言模型即時整理、摘要,然後彙報給所有參與者。最後形成的政策方案,獲得了超過 85% 的跨黨派、跨群體支持。從線上會議到立法通過,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,讓我們成為全球率先全面實施「廣告實名制」的國家。這正是 AI 作為「輔助智慧(Assistive Intelligence)」的最佳示範。
合作式 AI
Cooperative AI
這帶我們來到我們的核心策略。我們需要一個能與我們共同成長的 AI 願景,我們稱之為「合作式 AI」。
儘管許多關於安全的討論,都聚焦在人類控制 AI 的「垂直問題」上,但更大的挑戰是「水平問題」:確保一個充滿不同人類和 AI 的世界,能夠和平合作。如果我們沒有為它們建立正確的環境,即使是完美「對齊」的 AI,也可能被用於衝突。
合作式 AI 就在建立這樣的環境。這個創新領域聚焦於三大關鍵:創造能增進「人類合作」的 AI、設計安全的「AI 之間合作」的協定,以及為一個去中心化、民主的智慧體網絡,建立「具韌性的基礎設施」——能在你手機上運行,而不只在大型資料中心的 AI;其推理過程可驗證、可信賴的 AI。
這就是金字塔與網路的區別。金字塔很堅固,但其命運由頂層控制。網路具有韌性,其力量分佈在每個節點。專制是金字塔。民主必須是網路。一個去中心化、共生的架構,就是我們的防禦。
數位遷徙自由
Digital Freedom of Movement
要把「反社會」的平台變成利社會的公共基礎建設,有三把鑰匙:
「攜碼互通」(social portability):你的社交圖譜與內容要能即時帶著走,不被單一平台綁架。猶他州已通過《數位選擇法案》,要求社群平台提供內容與社交圖譜的可攜與互通,這是破除壟斷、降低攻擊面的重要一步。我稱之為「數位遷徙自由」:帳號的人脈與活動可攜、跨平台同步。
「橋接排序」(bridging-based ranking):X 的社群備註功能,用「跨立場都覺得有幫助」作為顯示門檻,實證顯示可降低不實內容擴散,並提升對查核的信賴。YouTube 與 Meta 也都已經在美國跟進。
「意義建構」(sensemaking):傳統民調常以簡化的題型框限討論,忽略了細緻的觀點。Google 與資深民調專家 Scott Rasmussen 合作的「We the People」計畫,正結合全美所有 435 個國會選區的公民,透過 AI 輔助進行開放式問題互動,從而發掘出深度見解與「罕見共識」,也讓少數群體能即時調整不利於自身的倡議,並獲得更廣泛且真實的支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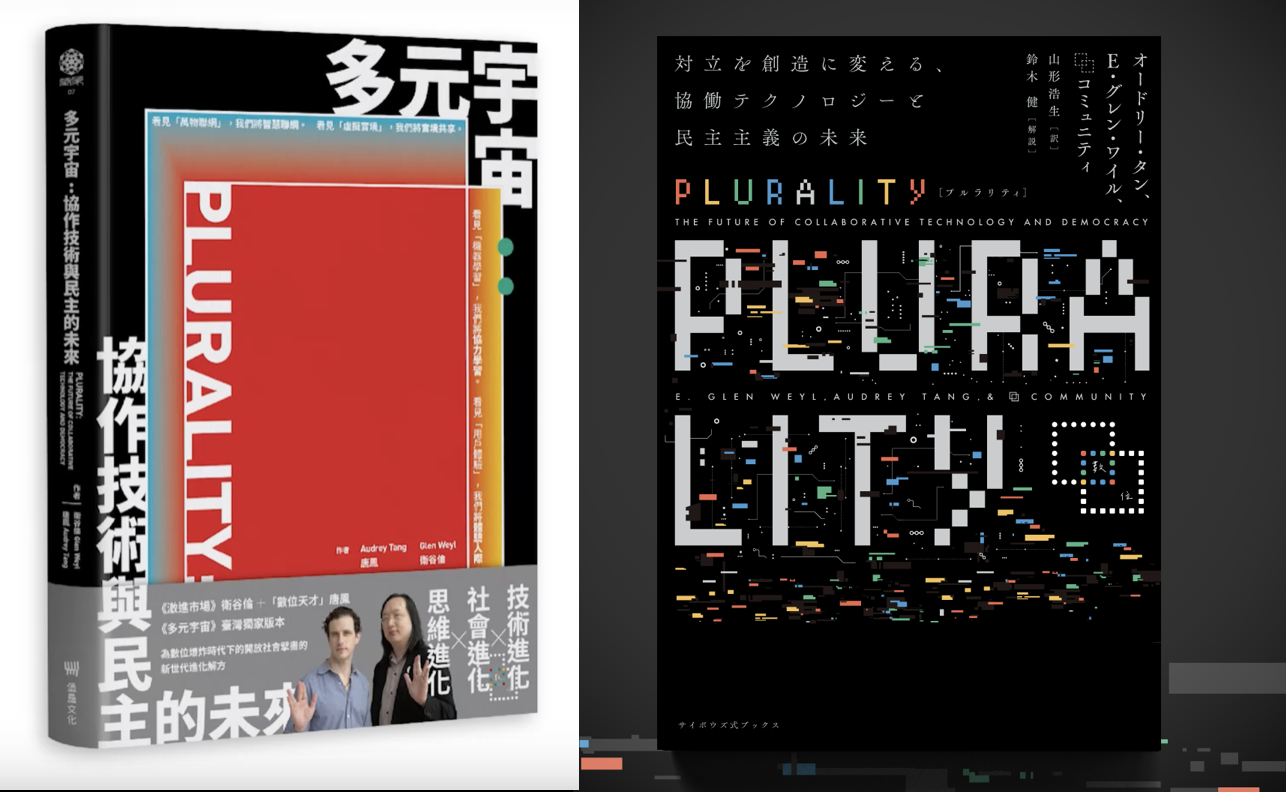
回到一開始的問題。面對 AI 時代的民主,我們該樂觀,還是悲觀?
在矽谷,很多人常說:「奇點即將接近(The Singularity is Near)」。
但我想說的是:「多元已經來臨(Plurality is Here)」。
「奇點」的想像是垂直的、是排他的,它把大部分人甩在身後。「多元」的想像是水平的、是共融的,它擁抱每個獨特的聲音。
民主,本身就是一種科技:一種讓我們能夠與意見不同的人共同生活的社會技術。而任何科技,都是可以升級的。
我們不需要等待完美的超級 AI 解決所有問題。我們需要的是更好的工具,來增進我們的「公民肌力」。
這個未來,不是由少數菁英或某個超級 AI 來決定。而是由在座的每一位,由所有願意聆聽、願意對話、願意親手打造的公民,共同決定。
The future is not singular; it is plural. 未來不是奇點,而是多元。
謝謝大家。祝生生不息,繁榮昌盛。
(本簡報內容以 CC0 1.0 拋棄著作權並貢獻至公眾領域。)